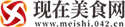(资料图)
(资料图)
文/李经纬
药物起源由不自觉到自觉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阶段。有关其起源的讨论也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帝王世纪》的作者、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淮南子·修务训》作了中国药物起源的传统论述,写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一论点为许多学者所引用和发挥。《史记补三皇本纪》认为:“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通鉴》也说:“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又如《通鉴外纪》也指出:“氏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有趣的论述,作者距今虽只2000年左右,然而其内容却是数千年乃至万年人们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尽管其中不无神话色彩,但确实是我国原始社会早期及其以后人们在寻求食物过程中逐渐认识某些药物作用的生动描述。按照我国历史进程,伏羲氏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的渔猎畜牧时期的早期;神农氏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农业出现的时期,约距今六七千年的时期。无论是渔猎时期的肉食,还是农耕时期的素食,或是更古的采集野生食物,都要有千千万万个人每天进行着数次,乃至无数次饮食的实践。所谓“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哪些植物之种子、根块、枝叶茎干可食或有毒,哪些动物之肌肤皮肉、内脏血髓可食或有毒,哪些湖河山泉之水等可食或有毒,这种先民必须不断实践的经验积累,是完全可以想象而相信的。可食者即逐渐用以充饥和营养。有毒者则逐渐地认识积累着毒性反应的情况:能使人眩晕,能使人呕吐,能使人泄泻,能使人汗出,甚而不止,能使人尿利,等等。这些毒性反应,也可视之为原始药性的感性认识,积累多了,重复出现多了,就会日益由不自觉的经验积累向着自觉的总结认识过渡,虽然这种过渡是十分漫长的,但这种过渡是不可缺少的。偶然中毒使腹胀、胸满等病症减轻或消失,人们逐渐认识了物质毒性与药性之间的联系,这正是药物起源的历史真实。这样的实践经验多了,药物从而得到丰富。
神农采药图
山西应县辽代佛宫寺木塔
摘自《中国古代医学简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